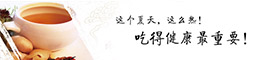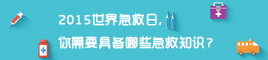1935年,中医《医界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封1933年行政院长汪精卫写给立法院院长孙科的私人信函,信中谈及有关《国医条例》的问题。汪精卫说:“此事不但有关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
此信一登,舆论哗然。有人讽刺说:“国医而能为国际体面而牺牲,则国医实有大功于国际体面矣!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国际体面不在赔款失地,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到底事件源起如何呢?
国医馆参与管理起纷争
《国医条例》是中央国医馆草拟的中医法规,希望通过立法来确定中医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诉求是争取中医行政管理权,即汪精卫所说的“授国医以行政权力”。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仍然将争取行政管理权作为努力方向。根据《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全国各省市均得设立国医分馆和支馆。不少地方的中医界都积极筹备,很快形成了一个“中央国医馆-省市国医分馆-县市国医支馆”的体系。甚至泰国、菲律宾、港澳地区乃至远到美国旧金山的华侨中医都组织了国医分、支馆,向中央国医馆备案。
这个体系能否成为国医管理自己的机构?在成立之初,不少地方理解为可以。广东一些县市国医分、支馆就试图直接参与地方医药管理。涉及医药行政事务的问题,在各地均有出现。由于涉及到具体利益,而且这些管理职能于法无据,就引起一些中医团体抗议。如上海国医学会向行政院上书抗议该地国医分馆“勒索”及“自称行政机关”等。这些都迫切要求对国医管理权的问题有一个明确说法。
争取行政管理权受挫
自1930年公布《西医条例》以来,有关中医始终未有正式法规。1932年,中央国医馆函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要求派员审定《国医条例》而未有结果。次年6月,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石瑛、叶楚怆、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等29人,在国民党召开第306次中央政治会议时提出了“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上所拟的《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和《国医条例草案》。
中央国医馆这一要求,立刻遭到西医界群起而攻之。有人认为“国医”这个名称,并非不可成立,但“尚欲超出中央卫生行政机关范围之外,自行管理国医”,西医团体纷纷上书指责其为“破坏卫生行政系统”之举。这些意见还得到部分政界人物的支持。在会议上,议案就遭到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汪精卫声称“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双方争论激烈,最后会议议决将《国医条例(草案)》送交教育、内政两部审查。内、教两部收到提案后,借口国医馆非行政机关,须由“充分具备现代医药学术设备的机关担负整理中医药学术的任务”,以及“现在中医中药之管理,均已有法规分别颁布”等理由否决了该案,并将原案转呈行政院。1933年6月27日,行政院举行第112次会议,以国医馆为学术团体,不宜管理中医,再次否决了此案。
这样,国医馆争取行政管理权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
《国医条例》变身《中医条例》
中央国医馆仍寄望于《国医条例(草案)》能在立法院通过,为中医明确法律地位。焦易堂当时兼任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他利用这一有利身份,在开会讨论前走访各委员,解释其中因由,使此案在法制委员会会议上获通过。但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全体大会时,因分歧较大而未通过。在一次会上,双方争执不下,致令焦易堂声称要辞职,可见当时斗争的激烈程度。
会内会外争论的焦点除了中医管理权,还有“国医”这一名词。当时反中医的学者傅斯年曾说:“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错了……我只提醒一句,其实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丢国家民族的丑了!”
而焦易堂则这样解释:“‘国医’这个名词,在我们中国向来是没有的。自从西洋的医学传到我们中国来,为要避免和西洋医学混同起见,所以从主体上特别提出‘国医’的名词来。这好比我国的文字本来无称为‘国文’的必要,因为同时发现了英文、德文、日文等不同的诸种文字,于是主体提出‘国文’一个名辞是觉得非常的必要。国医的意义,亦就是这样,切莫以为加上了一个国字,就是十足的代表狭隘的国家主义。”
但是,这样的观点终于未能为大多数人接受。汪精卫致信孙科正是在这一时候。幸好孙科对中医较为客观,在1933年12月15日在立法院召开的第三届第43次会议上,作为妥协,《国医条例(草案)》更名为《中医条例》,将中医的行政管理权隶属于行政院下的内政部,这样才获得通过。
立法院通过的《中医条例》却迟迟未见行政院公布,汪精卫主导的行政院,以不作为来消极拖延。中医界在1934年国民党笫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时发起游行请愿,亦无结果。
1934年底,中医杂志忽然纷纷登载了一条新闻——“汪精卫现亦信仰国医”。原来,这一年汪精卫的岳母患了阿米巴痢疾,西医屡治无效,不得已延请著名中医施今墨往诊,当时西医认为不可能用中药治愈,但结果施今墨处方却是“一剂知,二剂已”,两日即治愈。汪精卫也不由信服,制送“美矣良医”匾额感谢施今墨。
历史会是这样被偶然推动吗?汪精卫虽然于1935年12月卸任行政院长,但次年1月22日国民政府就正式训令公布了《中医条例》,应该还是他任上放行的。条例颁布后,“中医”成为正式法定名词。尽管中央国医馆作为一个机构名称仍然存在,但由于没有行政管理权,即使仍然冠以“国医”之名,其性质已与一般的社会团体无异。这说明在名称方面,政治和法律多方博弈的结果,仍然是以“中医”、“西医”并称最能为社会接受。而在行政管理权方面,《中医条例》原定中医由内政部管理,不久由于卫生署坚决反对,1936年底就修正,改由卫生署管理,但在署内设立相对独立的中医委员会专职管理。
一国有两种医学,能不能有两套管理系统?西方各国没有这种情况,中国能不能自行创设?汪精卫本来认为这样会有失“国际体面”,但一经见证中医的疗效,也终于肯接受中医了。可见作为医学来说,疗效才是硬道理。
不过,假如中西医行政各行其是,在公共卫生方面确实会出现问题。客观地说,要想单靠传统形式的中医来完全地承担已经近代化了的中国社会的公共卫生职能,确实是不现实的。但这不等于要歧视甚至废除中医。放眼新中国以来实施的中西医并重政策,在教育和临床让中医兼通适当的西医和公共卫生知识,就取得了积极成果,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今天我国的中医同样具备了应对传染病的知识和能力,在近年的几次公共卫生事件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都被列为定点治疗单位,在正确防疫的同时又能发挥中医治疗所长,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治疗SARS的战绩,都为世界卫生界所瞩目。可见,卫生行政如能合理解决好两种医学共存互补的问题,恰能长中国的“国际体面”,这或是当年曾执意压制中医的汪精卫所意想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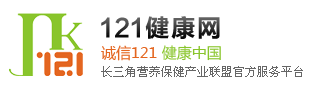

 揭秘印度生意最火爆的代孕工厂
揭秘印度生意最火爆的代孕工厂 虫草中添加“伟哥”?专家称无检验依据
虫草中添加“伟哥”?专家称无检验依据 火锅、小龙虾越吃越想吃? 地餐馆调料检
火锅、小龙虾越吃越想吃? 地餐馆调料检 实拍妇科实习全程:女人越漂亮越容易得
实拍妇科实习全程:女人越漂亮越容易得 英女子得了“睡美人症” 每天清醒两小时
英女子得了“睡美人症” 每天清醒两小时


 别对疾病的小信号视而不见
别对疾病的小信号视而不见 美容觉可以改善脸色 打鼾却让你老丑笨
美容觉可以改善脸色 打鼾却让你老丑笨 盘点乳房太大对女人带来的健康危害
盘点乳房太大对女人带来的健康危害 罂粟壳吃了有什么感觉
罂粟壳吃了有什么感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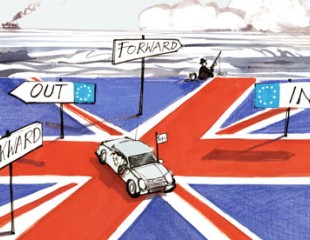 英国脱欧,对我国营养保健产业的影响
英国脱欧,对我国营养保健产业的影响 雾霾下的自救方案(2017版)
雾霾下的自救方案(2017版) 萨德对中国保健食品的进出口有何影响
萨德对中国保健食品的进出口有何影响 日本核辐射地区生产的食物吃了怎么办
日本核辐射地区生产的食物吃了怎么办 H7N9病毒中话鸡肉 产业安全促发展
H7N9病毒中话鸡肉 产业安全促发展 长三角营养保健产业联盟信息专报(3.15
长三角营养保健产业联盟信息专报(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