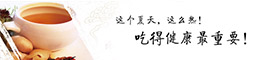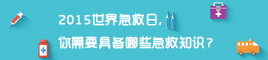张正良 /文
进城了,还扎下根,想回乡创点业,回乡久了,又想进城憧憬一下未来。总之,不管是郑波、老奎的回乡创业,还是柱子的进城回乡又进城,永远不变的是乡情,还有讨生活憧憬美好生活的动力。
“有人愿意一起回老家混不?”
酒过三巡,郑波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略略欠身,一饮而尽。“今天请大家来,没别的事,就是想咱村里几个聚聚,借这个机会,也想请哥儿几个帮我谋划谋划!我呢,就以水代酒,先干为敬。”
“哦,回老家?你打算干什么?当地主?”
“初步打算是这样,回去先弄200亩地,种上百来亩薰衣草,搞个小庄园什么的,再种点有机蔬菜,养几头猪,或鸭子鸡鹅,搞个农家乐。”
“你郑州的生意怎么办?两头跑能忙得过来?”
“前几天已转给别人了!”郑波说,“还有点股份在里面,先周转着,老家的事能做好,就全部抽出来。对了,郑春大哥,你从工信厅能不能搞点项目款把咱村门口池塘推一推,塘都快淤平了,我想整一下,养点鱼,种些藕……”
郑波
两年前,建材市场看上去还很风光时,郑波就萌生了退意。
2009年,因为弟弟在南方开了一家管材厂,郑波只好被牵进建材市场,在郑州东建材开了一家门店。好在,时机还不坏,正赶上楼市飘红,生意没经过反复就进入快车道。那确实是一个造富时代,每天一睁眼,传进耳朵最多的就是谁谁又搞了一个什么项目,运作开了,发了一笔横财,谁谁跟人合伙拿了一片好地,正在四处化缘,一开盘就是十几亿元,谁谁撞了狗屎运,跟某银行老总攀上关系,一下子接了几个在建小区的水电装修……眼见着身边一个个大神们今天还在浪迹天涯、混吃混喝,明天一转眼就成了坐拥几百亩上千亩地的地产开发商,今天还在夹着公文包溜街边,跟各色人等套近乎,明天就“大奔”开道组建团队扯起一杆开发公司的大旗。项目连连看,神话满天飞,郑波看得眼花缭乱。
没人跟钱有仇。混迹在老乡同学间,除了兜售管材,郑波也转接一些占用资金不大的地产项目做,利不多,但也都是挣钱的营生。可惜郑波是个老实人,有一分钱,就做一分钱的事,不太敢想一角钱的买卖,更没空手套白狼的胆魄,因此错过很多成长为大老板的机会。郑波也不懊恼,别人四处涮车坐时,郑波开着自己的黑色别克出去谈生意,别人都开上大奔、宝马、宾利了,郑波还是那辆别克。
但身在建材市场,郑波心里总不太踏实,这行当就像是一只被放飞高空的大气球,虽然你手里拽着线,但飘得太厉害,说不定哪天就没影了。“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郑波脑子里时不时就蹦出这句话,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小时候看连环画,翻到一老人对着荒坡哭诉繁华易逝,他的心都凉了。
一次,陪生意上的朋友到豫南游玩,吃饭时,朋友把一干人带到一处四野荷香的农家院。时至中秋,荷叶田田,莲子青青,碧绿满眼,清香盈鼻,而菜是极家常的小菜:萝卜炖土猪肉、地皮炒笨鸡蛋、蘑菇炖土鸡、清蒸大白条、豆皮炒小白菜……全都是农家自生自长的玩意儿,没有海参翅鲍,就地取材,简简单单,却吃得味浓情深。
那顿农家饭彻底触动了郑波的心思。回郑以后,他很郑重地给老家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一定要回来吗?”父亲问。
“一定!建筑这行当眼看就走到尽头,也就三五年光景了,不转不行啊!”
“那行,我想法给你张罗张罗。”
张罗归张罗,父亲并不希望儿子回去。农村人眼皮子浅,你从村里进城,村人高看你,你若从城里打道回府,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弄得不好风言风语的都来了,他这村干部的脸也没地方搁。但儿子铁了心要回来,做父亲的只能尽量给他铺路,话说回来,这些年农村也不难过,用地成本也不高,说不定还真能弄成点事。
村里的地都是现成的,谁家的地,打个招呼就成,也不需什么成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村里的年轻人一茬接一茬地出去打工,有能力的早已安家他乡,没能力的也在镇上或县城买了房,没人愿回来,村里的老弱病残则是种地的主力军,如果不是机械化作业基本普及,这些主力军们只怕早缴械了。
父亲盘算了一下,村里撂荒的地不少,弄个二三百亩还是没问题的,关键是拿地干什么。
“干什么都可以,干什么都比荒着强啊!”郑波这样回答时,对经营土地还只停留在概念上,未来具体要干些什么,能干些什么其实并不清楚,直到有天参加完北京一商业伙伴女儿的婚礼,他心里的农庄才有了雏形。
婚礼是在朝阳区一家大酒店举行的,酒宴结束后,主人特意安排远道而来的贵客到不远处的蓝调庄园游玩。四季果庄,古堡温泉,会所以及湿地,到处都能打动人心,最妙的是数百亩薰衣草营造的蓝海,人行其中,恍若隔世,那种震撼是郑波从来没见过的。
“妙不可言!”事后,郑波曾向父亲追述当时的感觉,“土地真的是太神奇了,没高山,没深水,一样可以创造出人间绝美!”
“我不知道啥叫薰衣草,你想种先得搞清它的习性,咱村的地适不适合,你可是从没种过地,不能光拍脑袋,想好了再作决断。”
“老奎不是在家吗,他这几年一直玩着地,应该对村里的土质很了解!”郑波想起老奎,多少有些兴奋。
老奎
老奎比郑波大十几岁,两个人各跑各的道,在村里时,没什么交集。
老奎算得上是村里的能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被村人唤作毛孩子的老奎窜到县城跟人学了几个月美容美发,回到村里就掀起了头发革命。小青年们一见老奎带回来的美发工具都有些傻眼:从来剃头都是一把手推子,外加刮胡子的一把刮胡刀,哪见过那么多玩意儿??牙剪、平剪、吹风、剪梳、滚梳、排骨梳、尖尾梳……原来理发竟有那么多讲究,发型也并不天然就是一个小平头,更重要的,女人也可剪发,也可把头发卷曲起来。老奎带回一股风,很快刮起来,不久,走村串巷的剃头师傅只能找他们的老伙计试刀了,而大姑娘小媳妇也试探着在头发上做起了文章。
也就一两年的工夫,街上到处都是理发店,什么新鲜玩意儿都出来了,连染发也不再稀罕了,至此,老奎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介于乡村间的理发大业也就寿终正寝了。老奎也不急,把美发的玩意儿收拾收拾又跟人学起了做豆腐。
村口有一眼宽井,300多米深,水质清冽,是当年钻井队探石油时留下来的。老奎人机灵,还在外学做豆腐呢,抽空跑回村买来下井的砖瓦、潜水泵、水管之类把油井修葺一新,待到学成归来,在井边盖一简易棚屋算作作坊,就开始了磨豆腐的营生。刚学的手艺,做出来的豆腐还欠些火候,邻村做了几十年的“老豆腐”只要在村口一出现,老奎当天做的豆腐就基本上得自产自销,要不,就得挑着担子到别的村串串。那时村里村外好吃两口豆腐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留下的不是舍不得花一分钱的老头老太,就是做不了主的娃娃妮子,三里五村的转一上午,老奎也卖不了几块豆腐。
乡村里的人日渐稀疏,正晌午头上,老奎转几个村子,吆喝半天,连个人毛都见不到。这样的生意叫谁都心灰意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老奎做不下无人生意,干脆把豆腐坊一封,带着老婆孩子出去打工了。
掏过煤,干过砖窑,也当过矿工,总之,凡是农村人出去干的苦活累活老奎几乎都干过,老奎是个很惜力的人,转了一圈,没像别人一样落下一身病,但也没能挣下钱,糊口而已。在东北帮林场伐树,树倒下时反弹回来撂倒了几个工人,老奎死里逃生,从此不愿出苦力,只想干点讨巧的活。
老奎打工也有过春风得意。在北京平谷一家毛衣厂,精于计算的老奎被老板看中,当起了小领班,订单过来,老奎负责计算客户要求的尺寸,不能有丝毫偏差,然后把数据送给不同的车间。干了三四年,没出过一次差错,老板很赏识,每单活干完,老奎都会收到一个小红包,20世纪90年代中期,老奎一个月收入已超过两千,比下煤窑挣得还多,在当时也算是高工资了。
但老板的生意一直不温不火,老奎的工资也始终没突破三千元。眼见着跳槽南方的小老乡都比自己拿得多,1999年老奎一狠心举家南下进入东莞一家毛衣厂打工。新东家发的是计件工资,老奎手拙,干不了多少活,但沾了过去当领班的光,一个月也能拿个三千多元,眼疾手快的媳妇倒是有了用武之地,林林总总,比老奎的收入还多,一家人在南方算是安顿了下来。
老奎恋旧,生活一稳定就想往回跑,就想他的豆腐担子、豆腐坊,想念浓得化不开的乡村味。“端人碗,受人管”,老奎不喜欢那种捆绑式的生活,每天的按部就班让他心里别扭,在家多好啊,想干什么干什么,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自己说了算,不用看别人脸色,人勤地不懒,养活一家人总不是什么难事。这样子给人打工终究只是一叶浮萍,早晚还得漂回去,何必呢?
如果不是厂里要进行产能升级,老奎或许还会一直纠结下去??虽说有心回家,但人过四十,夫妻俩都有份稳定工作也不易,况且俩孩子正上着学,处处都得花钱,回家未必能供养得起。厂里为在竞争中抢占先机,从国外花重金“请”回来一些机器,生产全部电脑控制,需要的人力大大减少。老奎学不了那玩意儿,看着电脑就头晕,人倒干脆,不待老板拉下脸,牵着媳妇就往回跑。
“就东莞那地方,整个一大工厂,哪里有家好?”有人问,老奎就这么答着。
老奎又开始做豆腐了。水依旧清冽,人过中年,老奎磨出的豆腐竟有了些味道,邻村的“老豆腐”几年前就谢世了,老奎成了“老豆腐”。豆腐不再是村里的稀罕玩意,老头老太也都吃得起,老奎的生意反倒红火了起来。
养猪的事,郑奎早先做豆腐时就干过,那么多白花花的豆腐渣,人吃都是美味,就别说猪了,不过,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猪崽很抢手,老奎就养母猪,指望着下崽卖钱,但时过境迁,如今村里早没了猪影,老奎就自己养土猪,一年出栏七八头,倒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养猪养鸡,肥料就多,老奎就想着种几亩地。水田种的是专家研制的特种稻,旱地搞的是西瓜种植,与种了一辈子地的老把式不同,测土、配方、施肥,老奎一样一样来,丝毫不含糊,不过两年,老奎比侍弄一辈子地的人都了解地的脾性。
地能生金,种啥都不会亏人,老奎认这个理,也有心多种些价值高的玩意儿,但老奎不懂市场,怕把自己的家底玩进去。
“奎哥,要不,咱几个合作,多承包些地,好好干一场!”郑波跟父亲沟通不久,电话就打到老奎那儿。
“好哇,哪几个?你一个,我一个,还有谁?”
“柱子!”
柱子
柱子在村里年轻人中算是见过世面的。
村里人出外打工,干的多半是体力活,顶多进个不错的工厂,旱涝保收,吃点花点年底了再剩点。柱子不是,柱子是结婚后出去的,媳妇的姐夫跟某大型油企华南区总经理有点瓜葛,柱子不进厂,而是到了深圳一家油站,没干两年就成了经理,媳妇在另一家油站做出纳,生活跟城里人基本接轨,平日交际也远不是打工仔的圈子。
从外出打工那天起,柱子就没打算再回村里。但造化弄人,不想回村的柱子最终还是带着媳妇孩子回家了??柱子正办着转正手续呢,老娘却意外去世了,不得不回来,照顾一病不起的爹。
半年后,爹的身心创伤得到了平复,可他的转正梦却泡汤了,经理的位子也没等他,柱子懊恼得不行,有心杀回去卷土重来,又担心老爹一人在家,心一横,反倒把媳妇也拉了回来。
柱子没心思种地,就把入城前做塑胶门窗的手艺捡了起来。好在,乡下的新农村建设正搞得如火如荼,每个行政村都在集中开发,柱子干的行当至少短期内还算是“朝阳产业”。柱子人实诚,又会来事儿,从不吃独食,有利大家分,讲求的是利薄人厚,因此总有干不完的活,一茬接一茬。
柱子的生意做不完,就雇人一起做。起先,有两人先后来当学徒,出师后就跟着柱子干;活赶在一起时,柱子会把师父请过来,好吃好喝好招待,每个月还奉上五六千元红包,师傅年纪倒是不太大,五十来岁,但早已不干这行,手生,出不了多少活,但柱子一直念着师傅的好,就是想师傅在那儿招呼着,自己干活也有劲。
不过,柱子看明白了大势,新农村搞基建很快就会到底,干不了几年,到时自己这手艺怕是没了市场,养家糊口都难,得尽早计议才行。
在油站当经理时,柱子曾结识一位药商,安徽人,在南方有一家制药厂,专做中成药,人很大方,花钱如流水。柱子向他打听来种中药材的情况,自己又专门跑到国内几大中药材集散地调查,钱花了不少,效果不太理想。2010年柱子试种了十几亩白术,前期长势挺好,突然就一片片地枯死了,找不到究竟,柱子眨巴眨巴眼,只好放弃。
柱子又平整些地开始种树苗,种景观树,种木瓜,种竹柳。树是个知道感恩的物种,你善待它,它就会可着劲长,竹柳已成林,木瓜也挂果,但柱子找不到买家。长势好的桂花在郑州每棵能卖1万元以上,可柱子的桂花树只能长在地里。
柱子从地里折腾不出来钱,有些心灰意冷。闺女都上小学了,再这样耽搁下去,只怕又得走自己老路,柱子眼看着乡里的教育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心里就发急,就想把女儿弄到郑州上学。
“真不行,咱得到郑州打工去。”柱子不止一次对媳妇说,“孩子耽误不起,大城市人多,要盖的楼就不会少,到郑州总能找到饭吃。”
柱子没心思在家干了,就三天两头跟村里出来打拼的人联系。
“波哥,你在郑州门路广,能帮找些安门窗的生意不?家里没什么干头,我也想到郑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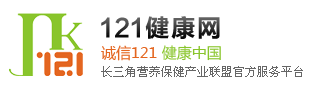

 揭秘印度生意最火爆的代孕工厂
揭秘印度生意最火爆的代孕工厂 虫草中添加“伟哥”?专家称无检验依据
虫草中添加“伟哥”?专家称无检验依据 火锅、小龙虾越吃越想吃? 地餐馆调料检
火锅、小龙虾越吃越想吃? 地餐馆调料检 实拍妇科实习全程:女人越漂亮越容易得
实拍妇科实习全程:女人越漂亮越容易得 英女子得了“睡美人症” 每天清醒两小时
英女子得了“睡美人症” 每天清醒两小时


 别对疾病的小信号视而不见
别对疾病的小信号视而不见 美容觉可以改善脸色 打鼾却让你老丑笨
美容觉可以改善脸色 打鼾却让你老丑笨 盘点乳房太大对女人带来的健康危害
盘点乳房太大对女人带来的健康危害 罂粟壳吃了有什么感觉
罂粟壳吃了有什么感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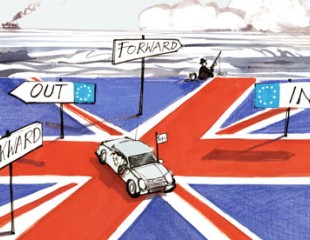 英国脱欧,对我国营养保健产业的影响
英国脱欧,对我国营养保健产业的影响 雾霾下的自救方案(2017版)
雾霾下的自救方案(2017版) 萨德对中国保健食品的进出口有何影响
萨德对中国保健食品的进出口有何影响 日本核辐射地区生产的食物吃了怎么办
日本核辐射地区生产的食物吃了怎么办 H7N9病毒中话鸡肉 产业安全促发展
H7N9病毒中话鸡肉 产业安全促发展 长三角营养保健产业联盟信息专报(3.15
长三角营养保健产业联盟信息专报(3.15